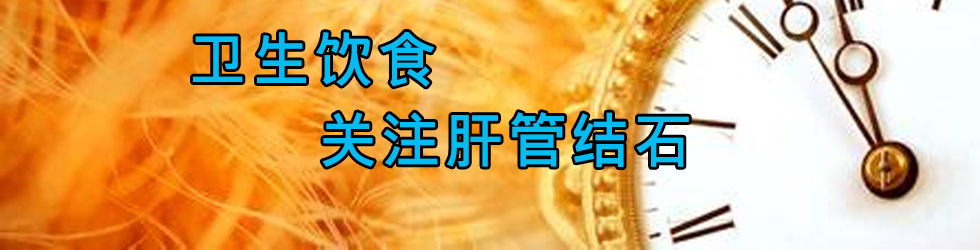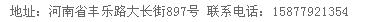记忆里有些声音很特别,比如轮船的汽笛声,日久弥新,至今忘它不得。
大新街位于淮河大坝的北岸,离我居住的村子有八里路,从下游的大柳巷到上游的蚌埠,每天各有一艘客轮往返于两地。大新有客轮码头,售票站设在大坝北面紧靠大坝,买过票就可以翻过大坝,到码头等候客轮的到来。蚌埠发往大柳巷的船是顺水,到大新就早,可是逆流而上的大柳巷过来的船到大新,天快接近中午了。正是因为这样,这艘客轮停靠大新码头前的汽笛声,就有了特别的意义。正在田里劳作的妇女们只要听到这艘船的鸣笛声,是不需要队长发话就可以回家做中午饭的,有时不知什么原因迟迟没有鸣汽笛声,女人们就会犯嘀咕,甚至有些泼辣的女人会把夹不上筷子的话说出来,引得男人们起哄骂娘。即便农闲的时候,只要客船的鸣笛声一响,男人就会对着自己家的女人说,还不赶快做饭,轮船都响过了。那时,家家都没有钟和表,把大新传来的轮船的鸣笛声,当成了报时钟,比队长的上工哨子声要好使的多。
特别是阴天或是下雨天,淮河里的客轮就好像是停在自己家门口一样,声音听起来特别近。甚至,连临淮关和蚌埠那边跑着的火车的汽笛声,也能听的到。
一九八二年的春天,太阳暖暖的照着生机盎然的大地,风暖暖的从田里游逛到我家寂寞的篱笆院落,每天放学到家我像个无头苍蝇,找寻不到一个可以落脚欢愉的地方。哥哥在五河二中复读,挑灯夜战准备着高考;姐姐在五河师范读书;母亲腹部时常会突然痛得额头汗珠直冒,多次医治不愈,父亲瞅准了农闲的时候,四处借了钱带着母亲去医院(当时农村医院),这下家里空落落的。
有一天,已读初二的我便有了一个现在看来很唐突的想法,去蚌埠找父母。这个想法冒出来,想念父母只是一个原因,另一个直接原因是与班里的“胡二楞”有关。胡二楞读书有些不照,可其父是个精灵鬼,生产队时就偷偷摸摸用秫秫(高粱)脱粒后的头做笤帚,去大城市上海卖,过去算是投机倒把也被批斗过,后来,土地大包干,他家的日子过得比村支书家都滋润得多。返回的时候,他从上海坐火车到临淮关,再转乘客轮到大新下。每次回来他都会带客轮卖的面包给他的儿子胡二楞吃。
这位外号胡二楞每次从书包里掏出面包,就像从书包里捧出一块狗头金子,左手托着面包,眼睛直勾勾瞅着面包外层上的包装纸,一路上,待人多的时候,他才会把包装纸撕开,表皮黄褐色的面包便兀自露了出来,他用右手慢条斯理的撕着,似乎很高雅地往嘴里放着,其实,胡二楞此时的一举一动并不笨,他是在炫耀只有他才有轮船上的面包吃……兴许,他要是大口大口地吃下去,我们这些孩子忍一忍也就过去了,可是他偏偏一小点一小点地撕着吃,烤面包的那种麦香和丝丝甜味,漫不经心地往我们的鼻子里钻,撩拨着每个同路者的味蕾。我暗暗地骂了句,狗日的二楞子!
正是因为父母在蚌埠,正是因为去蚌埠必须坐客轮,正是因为客轮上有胡二楞曾经吃过的那种面包卖,我就决定去一趟蚌埠。三叔看我一个孩子在家怪可怜,就偷偷从刚卖大蒜苔的钱里塞给我七八块钱,这也为那次也是第一次坐上轮船去蚌埠解决了路费问题。不过这是我的私自计划,不敢告诉三叔,否则,他不会放心我一个人去蚌埠的。
春天里,所有的鸟雀都起的早叫的早,可是今天它们没有我起的早,天麻麻亮我就地奔往大新赶。一路上一会儿想象着大轮船的模样,一会儿又想象着蚌埠的模样,其实,蚌埠我一次也没去过,哪里能想象的出来啥模样,只不过在一种那个时代的提包上,看到过蚌埠的图案,图案里有高楼有汽车有火车,后来感觉那应该是以蚌埠火车站坐为背景画出来的,一路上想象蚌埠就是图案上那么大个地方。
从大新到蚌埠的票价今天已经记不起来了,恍惚觉得不会超过两块钱,买好票,我就跟随大人翻过淮河大坝去轮船码头候船了。
汪曾祺在《露水》一文中提到“三大慢”:等人、钓鱼、坐轮船。其实,等轮船要比坐轮船慢得多。当人们看到从东面驶来轮船的轮廓时,天已经快临近中午,人们开始骚动起来。肩扛的,肩挑的,手提的,每个人都做好了上船的准备,我很简单就背个黄书包,里面放本书。汽笛声响起,烟囱里有股股黑烟冒出,轮船做着靠岸前的冲刺,浪花翻卷着扑打着岸边……船靠岸,船员们扎好大铁锚放稳跳板,便开始先下客再上客,大新算是小站,上下客都比较少,很快轮船就起锚向蚌埠方向前进。
上了船便是中午了,船舱里工作人员开始卖中饭,主食就两样:两角一碗的机压面条和一角一个的烤面包,零食就是小饼干,一角二分一包。当时人们吃的都是家里人做的手擀面,能吃到机器压出来的面条,感到特别的新鲜,那时的人跟现代的人喜欢吃手擀面刚好相反,基于此,我常会大喊:人啊人!我舍不得吃上一碗热腾腾的上面漂着葱花的面条,也是为了实现这次去蚌埠的目的之一,也是想和胡二楞比一比,俺也吃过面包哩!我于是只买了两个面包大口的吃起来,面包做的宣,气孔多,松软,一个面包没几下就吃完了,剩下一个我没舍得一下子吃完,待过了临淮关和十里城两个站,我才把剩下的一个吃进了肚里。面包的那种松软和香甜,至今仍在记忆里恋恋不忘,今天的面包从原材料到做工,花样繁多,可是,口感远不如那时的面包。作家王安忆在小说《蚌埠》里也承认面包和面条在当时是稀罕物,只是她说面条寡淡无盐的,面包是粘牙的,是面捂了,还有面没烤熟。面条我没吃,我不能枉下结论,可是面包我是吃了的,感觉很好吃,并非捂面所做或是没有烤熟,可能人对某一物的感知是因人因地的不同而不同的。记得船仓里没有座位,人们都席地而坐,也有索性躺着眯起了眼睛……拉二胡的,打莲花落子的,耍猴子的都有,我们学校勤工俭学组的郭老师还在船上推销起当时制做的膏药,膏药名字我至今仍能记得“永生一号”和“永生二号”、“济生一号”和“济生二号”,主要是治疗疥子的,贴到患处,使脓血彻底的从患处顺畅地流出来。
客仓里人多,还有吸烟的,所以气味混杂难闻,多数的时候我都是顺着悬梯走到船的甲板上,看淮河两岸的风光。到了古镇临淮关,最早看到的是淮河北岸属于五河县管辖的临北人,清洗着一筐筐牛的内脏器官,接着才看到河南岸属于凤阳县管辖的临淮关人,则把一车车蜂窝煤用平车上渡船运往河的北岸。我至今没明白为什么很小的十里城居然设置了停靠站,十里城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岸齐刷刷的陡峭,没有缓坡。
当轮船停靠蚌埠码头的时候,红红的夕阳快要落山,下了船的人们很快融进了熙熙攘攘人流。第一次去蚌埠我也是没有胆怯和猥琐,记得父亲无数次说过的话,“路在嘴上”,意思是去哪里,要多问人。记忆里经过国强路,而且看到卖炒好的瓜子和花生都是一口袋一口袋的摆放在那里,感到很新奇,那时我就喟叹原来城人吃瓜子和花生比俺农村人还方便嘞!
医院门口可巧遇到父亲去买烟,母亲看到我时落下了泪滴,用手摸着我的脸和头。父亲把母亲体内取出的石块拿给我看,说,胆结石,这下你娘没有胆了,被切除了。父亲说着,一脸的无奈。我拿在手里篮黄色,外形,大小,跟鸡蛋差不多。那时小,我不明白人肚子里怎么会长出石头呢?人的胆囊才多大啊!这么大的结石长在里面,娘要忍受多大的痛苦啊!平时看到娘总是默默无闻地忙碌着,我们看到的始终是那张微笑的脸,看来痛苦她都是背着我们自己硬撑着的,娘啊!想想娘的苦,我也控制不住泪水……
在母亲住院的那段时间里,我又陆续去了几次蚌埠,逛过二马路,逛过百货大楼,逛过天桥,逛过新华书店。若干年后我和另一个文学爱好者还去过当时的《蚌埠报》社,记得是春节刚过,冰天雪地的,天很冷,副刊的杨春云编辑接待了我俩。很遗憾,至今对蚌埠的印象就这些地方,至于火车站,每次总是匆匆而过。
一九八二年没多久,五河至蚌埠的公路通车,水路客运渐渐失去竞争力,客轮很快就停止营运了。
今非昔比,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,很多人愿意花钱去旅游。我想,如果这段水路能开通旅游观光船,集旅游观光为一体,品尝淮河里的鱼,享受淮河两岸特定的地域历史与文化,岂不是件美事!
(图片/来自网络)
张新文,笔名:雪莲红红,安徽省五河县人,居苏州,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。